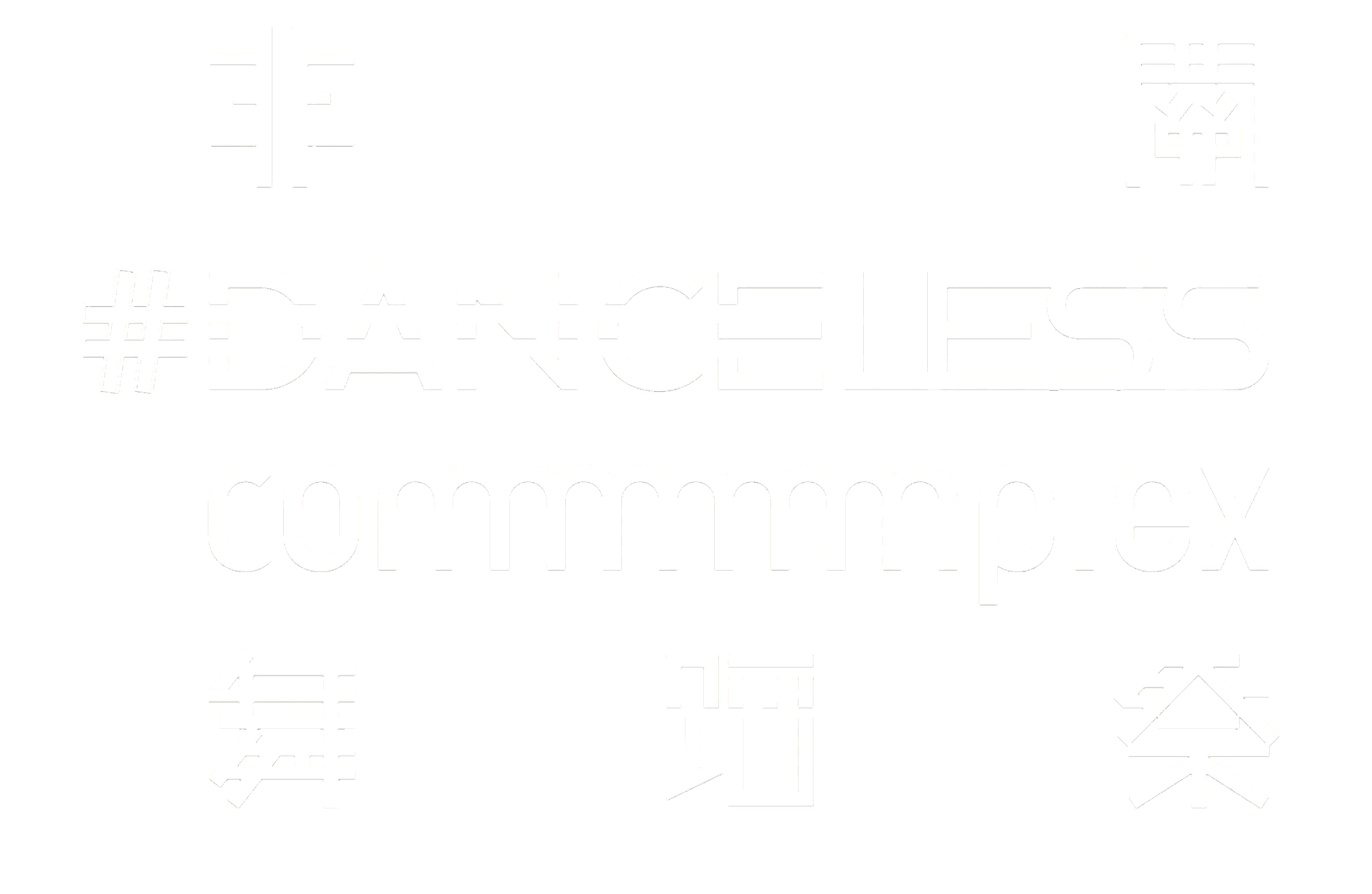舞蹈書寫終結篇
由初期的大頁印刷品到中期的網上札記,雖然形式上有討論過,但呈現還是各自表述為重。以文字去對話、交流和討論,則到了這兒才實踐。用WhatsApp作為平台,動機有二,一則取其時間上的靈活性,一則「我手寫我口」可能可以在言語和書寫之間,製造多一點空間。以下是沿著時間線的原文照錄,除了討論內容,還可看見溜走了的時光、情緒的變異、態度的轉向等等,換句話說就是過程。對話也好,交流也好,討論也好,去到最後,關鍵都在於人吧。這樣說很陳腔濫調,對不對?但我近來對陳腔濫調着實好奇,簡單如那有若金剛不壞之身是從何而來的?
黃大徽
Dick:
想跟大家談談「非關舞蹈祭」原本想帶來香港的五個作品。雖然因為疫情我們最終只能在網上觀賞,但它們始終是原點,肩負引進不同編舞方法學的使命。不如大家先從印象出發,講講當中最深刻的一齣舞作。
Yan:
我在策展舞碼中收穫的最初印象便是「重複」。當然我也沒天真地認為類似字母、代碼的重複會是一成不變的;而舞蹈中形式動作的重複,在位移間的確具有令「差異」得以浮現的優勢。
Ayelen Parolin的Autóctonos II依憑身體自帶一種隱喻,祛除任何戲劇性的手法,只向觀眾呈現重複本身。但危險的地方在於,「重複」在跨文化交流中,「重複」自身走向了極端的境地,即「重複」從自身抽象出來,喪失了意指的能力,只能在重複中不斷消耗能量。因此我的問題是,以身體作為隱喻,欲圖回應社會機器;那麼隱喻的方式是否需要脈絡化?社會是否僅呈現為一個普遍概念,而不是異質的聯結?
注:根據詞源學,Autóctonos【(autós,”own”) + (khthṓn, “land”)】本就具有「在地」(indigenous)的意涵
﹒
﹒
﹒
﹒
﹒
﹒
Dick:
五個作品相比之下,我對Choi x Kang Project的 Complement 最有印象,因為它理性得來不失幽默,計算得來卻又像有點兒戲。作為觀者,一旦好奇心被挑起,就會開始在現場演出和錄影之間追逐,似是參加了一場遊戲,最終有沒有破解到當中的程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過程中很可能引發關於perception的思考。這種創作方法在香港的舞蹈圈比較罕見,而Ayelen Parolin 的重複,由Pina Bausch 到 Forced Entertainment 均樂此不疲地應用過;Adrienn Hod 的 Solos,則令人想起德國舞蹈劇場;蘇威嘉的《一盞燈的景身》是我們熟悉的東方身體觀;至於Henrique Furtado + Aloun Marchal 的 Bibi Ha Bibi,形式就很接近上世紀九十年代興起的 physical theatre。
Dick:
大家幫忙幫忙,星期六前要完成啊🙇🏻
Brian:
單從印象出發的話,最深刻的一齣舞作是《自由步 ─ 一盞燈的景身》,原因如下:
疫情肆虐期間,隨著文化場所的關閉,大家都在思考「我們與藝術的關係」,提出包括「劇場/博物館有何意義?」等提問;
《自由步 ─ 一盞燈的景身》發生於一個非典型的場域,表演者與觀者的距離來得更近;在一個熙來攘往的街頭,環境或者有點紛擾,觀眾的焦點卻是更加集中(也許必須如此才能成功聚焦),表演者與觀者的連繫及交流也因此並不一樣。
Dick:
這種用WhatsApp討論的形式好似好難搵到共同的節奏。大家有乜睇法和建議?
Brian:
汲取開節紙的經驗(用signal 訪問兩位節之重心策展人物),都能夠有效展開到「對話」,當時其中一個house rule是「有限時間內作答,否則就飛過」,時間性會否都有關係?
Dick:
謝謝Brian。其實有諗過係咪約個時間,傾個零兩粒鐘然後做transcript,但WhatsApp呢種「我手寫我口」的方式比較符合「書寫」的意義,只是六天下來連一round都完成唔到,要做稍為substantial的討論可能要兩個月。如果話每個人出兩條問題,然後大家自選其中四條或全部來答會唔會好啲?因為如果只是我出問題,我會分不出是大家未有時間/未想到或不想答。除非大家覺得我們可以用這兩三天一氣呵成去完事,不然星期六是趕不上的。而假如趕不上的話,大家其實可以再想想怎樣wrap up -繼續用WhatsApp不過訂立house rule;返回各自wrap up的方向去;又甚至不用wrap up。。。這些都是可以討論的。
Yan:
如果不用等所有人都答完第一個問題。那我嘗試接著感興趣的話題寫。
Yan:
Dick嘗試給出一些脈絡。這對我來說很有趣。其實想瞭解歐洲表演界對「重複」的理解去到什麼階段?Pina和FE的時間都不算太近,與Ayelen相近的藝術家,他們之間的比較會如何?這裡牽扯到一個寫作的方法,也是我自己的盲點,那些「過世的」「白人」「男人」的理論意味著什麼?借用他們的概念來寫作能得到什麼?我要同死人對話?或是我同香港寫作人之間的溝通要透過死人這個媒介來完成?
Yan:
Brian假設了一個場景,但這個場景未必符合《一盞燈》的演出狀況。我的記憶裡,《一盞燈》於台北至少在幾個不同場地演出,每個場地都個性十足。原名「中正廣場」的「自由廣場」;「國立故宮博物院」(時值院內正好在做一次明清生活的展覽)。如果按照Unlock原本的計劃,《一盞燈》也是要在大館進行的。這些場所的性質似乎都不隨機,反而是典型得有些過分,可以牽扯進一系列的社會討論。假如《一盞燈》去到西九,又會怎樣?因此,如果要書寫《一盞燈》的話,每個版本都要重寫,而我自己做不到。
Dick:
謝謝Yan。好的,我們又可以試試這個方式啊。
Dick:
我嘗試把你有關寫作盲點的問題修改了一下然後自問。『這裡牽扯到一個創作的方法,但那些「過世的」「白人」「男人」「女人」的作品意味著什麼?借用他們的概念來創作能得到什麼?我要同死人對話?或是我同香港寫作人之間的溝通要透過死人這個媒介來完成?』有關「過世的」「白人」「男人」「女人」,我們先別伸延到更複雜的層面去,例如「性別」「種族」「殖民」等等議題。我只想說那些「過世的」「白人」「男人」「女人」的作品曾經在我的formative years帶來過啟發,刺激過思考,甚至經過過濾和沉澱後,成為我作為一個藝術家,在觀看和實踐時的一些依據。他/她們是否「過世的」「白人」「男人」「女人」其實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和他/她們發生了連繫,而這些連繫幫助了我成為我自己。是的,有時在溝通上為了方便,會羅列一堆名字或流派作為參考,以期望最短時間得到共知,在面對不同的受眾時確實需要留意,但同樣地學院派的詞彙有時候也一樣。至於重複,作為現象/形式它本身是「中立」的,無分歐美亞非,只是應用有別,想詮釋的東西有別,有人把重複混合加速把滑稽轉化成暴戾;有人以不變的重複去彰顯現實中的無力感。Ayelen的重複對我來說也有意指的,如果我們認為舞蹈源於祭祀,遠古的祭祀是燒香令人進入一種trance,透過身體重複的踏步和扭動與神靈溝通,這符合作品名字中indigenous的意涵。
Lok:
我最深刻的作品我諗係同呀dick 一樣,都係來自韓國的組合。因為我覺得係video 作媒介,佢哋尼個性質的作品有最低程度的失真,溝通的係一個idea和一種明白,而其他所需要的血肉同感/共震很大,令video 所產生的距離更大。而complement 係思考的美學,令我的想像可以係唔同的角度補充失去的現場感。
Lok:
認為當代舞的討論是不可以完全離開’當代’尼個概念的發源地,意指西方哲學。就算解殖學說,其討論也是使用西方學術框架,不論是立是破。 當當代概念被使用,我認為不能避免使用西方歷史來進行立證、反對或舉列。
而西方的意識形態歷年來不斷改變,不斷有要求’進步’的行動,所以解殖的學說,反省自己的言論和舉例在香港變得重要,但我始終認為如果要完全摒棄西方美學/思潮來討論’當代性’(1) 是不可能的,因為除了根的當代必然不是當代而係其他思路。
Yan:
我覺得對話開始有趣。文字未必是我的身體或語氣。請大家原諒,以下文字沒有什麼情緒。
Yan:
讓Dick成為自己的一定包括那些女人,但這在我的盲目溝通中不存在,所以我才對這種溝通框架抱有疑問。我想說西方理論,如果要回到學術史裡面看,與「死」「白」「男」相對的東西都有助於打破原先的框架。重複作為哲學、動作(也許)是中性的。但「隱喻」不是,那麼,作為象徴交流系統的祭祀也不是,因此歐洲人去到澳洲,看到「indigenous people」(早一些用的是aboriginal),大家都搖頭晃腦,也許是要打起來的。(Dick的indigenous看起來有些牽扯到時間維度[甚至文明程度?]})但Dick說的「trance」要憑藉什麼而成立,我會覺得《出竅》離我近一些。
Dick:
想先問問「那些女人」的「那些」是那一些呢?而沒被包括的又是那一些呢?因為我不是從西方理論或學術史去談,所以「死」「白」「男」我就只從最接近字面或相反的意義去理解。我們每個人本身都是一個框架,也許要先看清楚自己的框架,然後才再想想是否要打破吧。而當我們是如此不同的框架的時候(有點像此刻的我和你),我們又可以和應該怎樣溝通呢?對我來說,indigenous令我聯想到遠古的部族,從而引申到祭祀時透過焚香進入一種精神狀態,令身體重複擺動,藉此與神靈溝通。當中重複是重點,並不牽涉「隱喻」或祭祀是否中性,甚至不涉及trance。我明白《出竅》會離你近一些,但如果你說的trance是指表演狀態的話,則《Autóctonos》或《出竅》都沒有去到那兒。
Yan:
各位早安
Yan:
基於個人經驗史的理解,將其作為書寫的原點,這對每位書寫者來說無疑是自然且真切的。回想我自己在此溝通的立場,也許是想反思香港目前舞蹈書寫的範式。如同阿洛講到,談論當代舞蹈,不可以完全離開西方哲學。然而,在這樣的哲學框架下,我自己的書寫多大程度變得僵化。所以,Dick呢?阿洛呢?Brian呢?你的書寫有潛意識影響的框架嗎?和香港其他人的書寫的差異呢?或是想尋求什麼可能?
Yan:
Dick,從你對indigenous與溝通的解讀,我看到另一種認識《Autóctonos》的途徑。這一點和Danceless的策展導言有些不同,其中說到Ayelen的作品質問的是群體的地位與歸屬感(而「身體作為隱喻」也是策展導言中用到的論述)。我反而是想從這個問題出發,去看看「策展導言——作品——另一個書寫者」所產生的書寫張力。你會怎麼想呢?
Brian:
(先想講一啲題外嘅題內話)尋晚見到訊息量開始增多,感覺係「溝通」隨即慢慢開始,去到今朝先有空間追番大家講嘅嘢,一方面發現有啲可能感興趣嘅位已經過咗果個參與時機,另一方面「溝通」真係好難,稍為睇咗大家嘅一啲對話,中間要去釐清、定義嘅東西好多好多,多到三言兩語都無可能講得清楚,同時每一段訊息中都有多個地方咁做,情況就更複雜(平日嘅書寫都會遇到呢個狀況);
仲有一個深切體會就係正當我闡述緊呢個點嘅同時,我就見到Yan 「輸入中」開展緊一段回應,感覺係層層疊疊永遠都追唔到成個流程(生活節奏愈快,情況更加嚴重);
我將呢個稱之為「題外嘅題內話」,原因係相對於前面溝通嘅「內容」,我自己對溝通嘅模式同效果覺得更加好奇(當然都可能同對於相關「內容」涉獵不深有關);
開始慢慢入番個題度,呢個群組叫做「舞蹈書寫終結篇」,當時所謂嘅初心之一大概係「以舞蹈書寫去睇下到底舞蹈書寫係啲咩」,而喺呢個群入面「書寫」同「閱讀」嘅體驗,係令我再開始諗有關「舞蹈書寫」呢個命題:
假設我係一個讀者,然後我被提供呢個群組嘅材料,我嘅閱讀過程會係點呢?雖然被提供嘅材料唔會再有實時變化,但係如果讀者因為各種原因錯失咗同有關內容發生關係嘅時機,身為作者又仲有無啲咩可以做?
特別係喺依家呢個節奏急促、瞬息萬變嘅時代,事件發生同結束嘅速率係比起從前以幾何級數咁推進,所有嘢都比起從前更易「過氣」,傳統紙本式、印刷式嘅書寫,仲有幾大嘅生存空間同價值呢?特別係當場刊之類嘅印刷品都變得可有可無。
直至呢刻,我諗我係對於「舞蹈書寫」入面點樣(How)有效(呢個位可能又要解題)「書寫」感到更大興趣。
(btw 一直寫寫寫,我係未完全睇晒Yan 嘅新留言,因為如果要睇埋先覆,可能永遠都會缺席)
Lok:
回應書寫僵化和框架的提問。我認為自己係一個十分僵化的人,有一些思維係十分難去改變,我對美學、藝術定義、如何創造和如何被接收有一定的立場。
雖然擁有個人意見和美學才能在群體裏分辨出自己,但我在進行書寫時,大多語言都想開拓觀者對作品的想像,以不同的角度(世界/宇宙)去欣賞或體驗或思考作品,擁抱可能性,以至不浪費任何有潛能的美和價值。
我亦認為僵化不一定要避免,要審視個人行為僵化對他者的影響。如在影響範圍內的社區根本不受其僵化文字影響或未曾理解僵化文字的本意,我認為重覆使用,等待社會對文字的連結,變成真係有base 才改變也無壞。
Dick:
我開始覺得興奮又懊惱。興奮是因為討論氣氛開始形成,懊惱是好像Brian這段字,可以引伸開去討論和思考的東西實在太多。經歷了近兩年的種種,在有天可能選擇以全然沉默來面對這世界之前,姑且就用講得幾多就幾多的態度回應。作為這次「舞蹈書寫」的facilitator,我的初心比較像「以舞蹈書寫去睇下到底舞蹈書寫’可以’係啲咩」,著眼點不在於尋找定義或重新定義,而在於可能性和多元性。其實也沒有什麼目標要達到,只是想製造個空間,等大家擦下自己和別人的邊。我也很好奇讀者會怎樣閱讀,正如我自己也沒有料到這群組內的dynamics會這樣發生。也許順著時間線去閱讀,他/她們可能比較容易揣測到「有關內容發生關係嘅時機」,但畢竟那是過程,幾多人有興趣成疑。觀眾選擇他/她們想看見的,讀者也是吧。舞蹈書寫是兩個界別的合成,對舞蹈或閱讀有興趣的人,當中又有會幾多對舞蹈書寫有興趣呢?至於有效這回事,在第一階段,即是在出版那張大紙時會想得較多,之後的札記和現在的終結篇都是試咗先算。
Yan:
Brian和Dick說完之後,我也更加意識到開啟終結篇的機會,是讓自己去思考溝通與關係。但這兩個層面在我來說,其實都是小範圍的,甚至僅限於我們四人之間。關於Danceless的書寫其實也不少,每次演出前後,除了這個小隊伍,還有許多人都貢獻了自己的文字。他們影響我多少?也許就變成我是讀者,就按照自己的喜好看看吧。然而,能觸碰到我的卻是Dick創造的這個空間,也是Brian所說的「不能缺席」,因為我覺得彼此之間有個責任。有些時候看到你們寫的東西,我特意選擇一些東西寫,或是特意不寫重複的;讀到某些想法,發現原來還可以這樣想,或是和已經想到的很有默契。我自己的文字,儘管沒有即時回應,但知道大家都會閱讀,只是不清楚你們的邊界同樣有被觸及嗎?我們在一起開會,一起看演出,偶爾見面也會聊一聊,沒有一次dynamics完全相同。我想著不如這次再嘗試其它的討論節奏,於是便有了「針鋒相對」的文字,也對各位不同的書寫意識有了多一分瞭解。
Dick:
不同不是很自然的嗎?不同不是就可以有多些空間去討論嗎?所以如何討論和溝通也許才是重要的,如果陷入了不是你對就是我錯的局面,最後通常就只剩下一種視野了。我覺得在表演藝術中,張力是永遠存在的,從舞台與觀眾席的設置,從創作人「主動地」去做作品而觀眾「被動地」去觀看,那其實已經意味著一種對立和權力關係。但有趣的是沒有了其中一方,演出就不會成立,所以斟介與周旋在這關係中是永恆的。
Dick:
在舞蹈/文化/藝術方面,我沒有接受過任何有系統的學院式訓練,一直都是以實踐和自學走來的。好處是擁有學習自主權,可以只跟隨我的喜好和好奇的方向去挖,但同時間亦可能miss out了好些理論的基礎認識。不過我相信,只要能回到事物的本質去,溝通的可能性就會擴闊。有關知識的功能,我的看法是用以轉化的,吸收過後經過整理、組織、過濾、沉澱,從而以自己的語言去建立一套看法和說法。我不知道這樣有否回答到你的問題,但寫到這一刻我想起在舞蹈書寫這團隊內,我們四人的背景不盡相同,文字是你表達以至工作的先決工具,因此其他文字也成為了你的参照和啟發的主要來源。
Yan:
今天看到一則關於「relationship」的雞湯文,所以還是決定在這場書寫終局裡,做一些自我反思。本來我是想逃避的,因為談話間讓我產生了負罪感,似乎我的字眼、行文,甚至是習得的知識,都變成了炫耀自己,傷害他人的手段。這有違本意。我參與該次實驗,並最後拋出疑惑,針對的是自己習以為常的書寫方式,例如常常使用艱深的概念。在互動中,我發現從概念出發並不能加深討論。但由概念轉移到討論溝通與思維方式,卻極具啟發性。我和Dick之間存在的是概念與實踐,以及個人經驗間的錯位;阿洛的理性文字反而鼓勵我正視自己的思維方式;Brian總是能跳出當下的衝突,另闢新視野。所以真要說我對這場舞蹈書寫實驗的本質的反思,恐怕是已經放棄了慫恿大家去挑戰範式,並轉化為重溫四人文字間的互動,梳理下關係的建立、試探與挑戰。結果發現,自己寫作,和別人單獨互動容易,四個人在一起總覺得少了些什麼。可這種集體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呢?我期待也恐懼下一次機會的來臨。在那之前,我至少明白了一些和大家分別互動所要注意的事情。說回那句雞湯,又是一貫的辨證,”No relationship is ever a waste of time. If it didn’t bring you to what you want, it taught you what you didn’t want.” 最後也算是辛苦完成了這項計劃,希望大家一切安好,很快再聚~~
﹒
﹒
﹒
﹒
﹒
﹒
Brian:
(階段式)結語
呢度嘅小小討論,正正展示咗一個「溝通」嘅過程:由「五光十色」充滿林林總總嘅主題、素材,慢慢過濾到、凝聚到個別範疇之中,先至開始有所互動;
當中喺同一個框架入面,各人因應各自背景內涵各有投入,其中嘅異同就係養份嘅核心,就好似當紅男子組合命名嘅典故,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一面鏡子,可以照見自己,以至係關於「舞蹈書寫’可以’係啲咩」嘅可能性,是為今次相遇最大嘅反思、得著。
﹒
﹒
﹒
﹒
﹒
﹒
Dick:
我的人生充滿疑問。每個作品、每個計劃以至每段關係的完結,留下來的通常不是答案,而是問題,有些成為未來探索的起點,有些加深了過往的迷思,有些膠住了。如是,在這個非關舞蹈祭的舞蹈書寫項目完結之時,我一如往常帶著問題前進,有關合作的,有關溝通的,有關身體創作和寫作之間的,有關找對人和做對事之間的。沒有答案其實幾好,思考會變成無休止的過程,有待實踐印證,然後又回到思考去,生生不息。
﹒
﹒
﹒
﹒
﹒
﹒
Lok:
過咗咁多日,終於下定決心寫關於尼次經驗的最後一段文字。尼幾日我都有不停問自己問題,究竟我自己點樣先可以再更加接近自己理想的自己,點先可以簡單地寫出自己對舞蹈的睇法,甚至希望自己可以有勇氣寫下本地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生在香港要對香港事物有公開表態很困難,希望我可以有一日能夠學會。